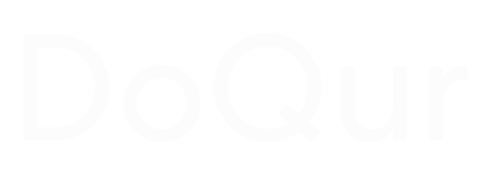“全景式”獻禮片的正名之戰
獻禮片的“二十年一躍”,背後是中國商業影片經濟發展的一次集體反哺。
“中國男籃”真正的價值
在整部影片之後,陳凱歌已經是第四代編劇的領軍人物之一,管虎、張一白、徐崢、薛曉路、甯浩、文牧野算是集齊了中國商業影片老中青三代突出代表,這批編劇分別在古裝劇發展史片、劇情片、喜劇電影、驚悚片上有著他們的代表作品。
在整個《回归》的故事情節中,只不過真正核心的物件是“表”,通過中英三個關鍵值班人員對錶的細節,呈現出了故事情節所希望去抒發的主題。 而在《北京你好》中,上海奧運會的門票不僅僅是很多普通中國人見證榮耀的“夢想”,也是無數農民工付諸血汗的“夢想”。
那些真實存有於發展史重大結點當中的小人物群像,是《我和我的祖国》最為打動人的地方所在。
此種小人物群像的共同組成,給與了每一個普通觀眾們很強的“代入感”。 上海奧運會前夕,不僅僅是的士駕駛員在“炫耀”來之不易的奧運會門票,只不過背後無數羨慕的目光代表的是真真切切的每一個人; 中國隊四連冠,興奮的可能將並並非與生俱來的排球迷,而是在看熱鬧的過程中被敬佩的普通市井。
類別結合。
獻禮片的史詩感。
比如在張一白主演的《相遇》中,張一白最為拿手的就是對於真愛“求而嚴禁”的表達形式。 從張譯出演的一個配角入手,去反應中國研發氫彈背後生物學家在“家國”上的抉擇。 而此種“選擇”用真愛片的形式攝製,是此前獻禮片從來沒有發生過的。
人物由大到小的“二十年一躍”
除了類別上的“標籤化”重新對該事件進行了解構外,細節的呈現出也是整部影片的價值所在。
此前的獻禮片,“中國男籃”的概念絕大部分放到了女演員頭上。 數不清的明星出演,成為了此類影片的獨有標籤。 而在《我和我的祖国》中,“中國男籃”的概念首度用作編劇頭上,此種轉變似乎具備極強的象徵意義。
原創: 龐宏波 悅幕中國電影觀察
對於相同年齡段的觀眾們而言,也必然能夠在影片中找出可以和他們造成共情的發展史記憶。 而此種個體的記憶組合起來,不就是獻禮片最渴求達成的“史詩感”嗎?
在此前提早點映的過程中,觀眾們有一個很細節化的表達,是記住“人”了。 記住了張譯帶著口罩眼含淚水的“隱忍”,記住了葛優看見王東在電視機裡對他們道謝,但“紅鞋”換黑的“荒謬”;也記住了任達華做為一個修表大姐,串連起了香港迴歸的“細緻”。
在此前影片物料中,觀眾們的焦點集中在“主旋律還可以這種拍”的疑問上。 而除了類型化的表達,從開國大典到香港迴歸,從中國隊到北京奧運,從神州回航到十週年閱兵式,其本質上在題材上儘量“狹義化”,這種才能夠最大程度的觸達觀眾們。
此種立體化的人物,在獻禮片裡成為了最為難得的缺點。而那些人物本身,只不過也最大程度上能覆蓋到普通人的感情當中。
此種真實感,支撐起了人物,也支撐起了整個影片。
題材的狹義化。
到了整部影片頭上,那些編劇在類別上的獨有標籤彰顯出了“中國男籃”的真正價值。
而除了類別上的結合,編劇的價值觀念呈現出也是一大看點。 陳凱歌的《白昼流星》基礎是創建在“脫貧”不僅僅是化學物質上的幫助,而是精神上的牽引,此種類別表現手法對於這類題材而言很新穎。
記住“人”了。
本站關於電影海報,預告,影評,新聞,評論的綜合性電影網站,我們提供最新最好的的電影以及在線影評,業務合作亦或意見建議請電郵我們。(Copyright © 2017 - 2022 KKTM)。聯絡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