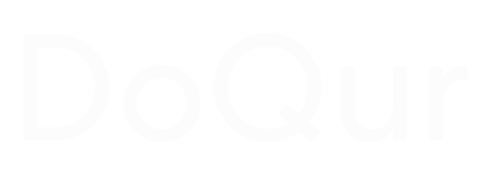回憶起《流浪地球》,所謂的“創意設計”,是中國電影的里程碑式
“我們好 ,我是原製作者穆穆講娛樂,專門為我們聊一聊好的娛樂及影視製作的這些人和事。
討厭的一座影片故事情節是,新政府把與否執行搜救火星的最後計劃做為現代人的一項自主選擇。希望與恐懼共生的活,與棄絕心靈放棄掙扎的死,我始終還是覺得,人是有個體選擇權的。莫斯的那句“莫斯沒有變節”,莫名覺得委屈巴巴。本想著人工智慧已經高級到有逃生本能了嗎?!還有它的那句“讓人類永遠維持理性,果然是奢望”,既有點兒嘲諷的好笑,又覺得壯烈的傷感。孤注一擲去博弈火星生存的可能將,還是保留火星文明延續的可能將,至少我在想的這時候是有一點遲疑的,但融合彩蛋服藥,還是尊重劉培強說的那一句“沒有人類的文明,不叫人類文明”。
以視聽盛宴吸引觀眾們,潛移默化的宣傳我們的思想和價值觀念,向全世界輸入中國的人文,價值。這才是我最喜歡流浪火星的地方,做為2019年被吹爆的科幻電影,承載著關上中國科幻電影發展史正門的重任,細節處理和宏偉的場面都很讓人觸動。在家看沒有3D效果,效果減半。傻乎乎的問一起觀影的人:我們的火星真的會變為這種嗎?一百代人的流浪火星計劃真的會存有嗎?
我覺得流浪火星漂亮,不單單是所謂的奇幻,而是中國思想,中國方式。讓世界看見了除了英國英雄主義以外的,一種更合理更可行的組織形式,解決問題的方式。而新冠禽流感,讓此種或許只存有於影視製作中,真實性存疑的思想和方式,在現實生活中實實在在的向全世界展現出,並經受住了考驗。但是在英國的陪襯下,更顯現出來其優越性。
以前看發展史總覺得為什么中國有那么多無名英雄,小人物英雄。只不過這只是一種必然。每一人都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每一人在最困難的最危險的這時候都可以挺身而出,那么如果困難和危險發生了,那么英雄必然會誕生,而困難和危險常常發生在第一線,自然一線上就會湧現出無數的英雄。
當預定的引擎已經被啟動,也並非任務完結之時,在動力系統完全足夠多前,找出未啟動的引擎,還有之後的單一突擊隊難以順利完成的這時候,快速想辦法共同組成新的大團隊,不一而足。那些想法那些操作,對於我們而言幾乎就是下意識地。而在影集中,差不多能望向天,嘴上說著要完了,接著等著英雄從天而降,困難只是為的是讓英雄更顯必要罷了。
在全球禽流感大背景下,重新上看,愈發覺得中國式組織的強大和合理。以往西方的英雄影片,挽救世界靠英雄,中央政府組織就是打醬油甚至是拖後腿的。全世界就指望那幾個人,你假如問假如不小心失利了怎么辦,問就是主人公光環,最後一定還要讀秒,不到倒數10秒不能玩。刺激嗎?刺激。有意思嗎?有意思。接著呢?沒了。爆米花影片嘛,再問你就是槓精。那什么是中國式搜救?不僅僅是飽和式的搜救,而是每一人兩組人都曉得明晰的目標,每一小組都有重大決策制度,依照實際情形調整,最終都為的是整個戰略目標服務。比如說故事情節裡的電池組出問題了,不代表任務失利或完結,找尋新電池組或是找出代替品繼續任務,不須要額外的指示,在戰略目標變化前,兩組人都會自行進行調整。
文章標簽 流浪地球
本站關於電影海報,預告,影評,新聞,評論的綜合性電影網站,我們提供最新最好的的電影以及在線影評,業務合作亦或意見建議請電郵我們。(Copyright © 2017 - 2022 KKTM)。聯絡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