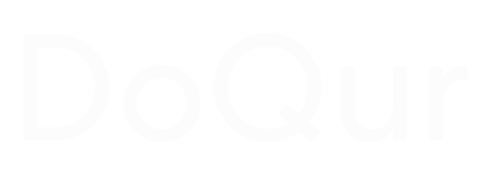立刻評|《父辈》的故事情節,值得更多地將講訴
《乘风》中的母親,是步兵團的副團長,影片在表現騎兵從青紗帳中衝向集結,和從敵後包抄登陸作戰時,採用了許多象徵主義的技法。這不但提高了影片鏡頭的娛樂性,也成功引起了觀眾們的共情心——美與唯美,愈發能襯托內戰的殘暴,一位母親的付出與犧牲,必須被很好地銘記。
《我和我的父辈》整部影片,就是把三代人的母親的爭取過程,串在一同講訴了出來。相同的觀眾群,都能自取所需,從裡頭找出又一次認識父輩的角度。
看之後,我故意屏蔽掉了與影片相關的各式各樣信息,並非害怕被劇透,而是想帶著一種陌生的眼光去欣賞它。在各式各樣文學作品中,父輩的形像,不免有被限定、被固化的成份,我想看一下《我和我的父辈》整部電影,能無法帶來許多新鮮感。
黃軒出演的母親,在荒蕪肥沃的地方從事人造衛星科學研究,儘管是一個神祕的職業,但母親依然是童心未泯的母親,他對他們的小孩說他們是個著名詩人,工作是在夜空上作詩。儘管他留給小孩的散文經典作品,僅僅是惡作劇般的在紙上寫了個“詩”字。
一個“無所不能”的母親永遠是小孩心目中的神,但就像片子最後母親毅然決然來到大海把溺亡的女兒託舉出水面一樣,《少年行》的價值觀念還是穿透了時間與空間,返回一個最為樸實的態度上——母親的臂膀,永遠是小孩降落的網絡平臺。
因而,在看《我和我的父辈》的這時候,趙薇編劇的五個影片之一《诗》,成功引發了我的共鳴。
沈騰編劇的《少年行》,用時空旅行的概念,包裝了一個相關母親的職責的問題,在整個影片爆笑的氣氛裡,沈騰輕鬆地解決了母親的新定位、父子關係、家校關係、子女教育等現實存在的問題。
國慶長假,看的首部影片是《我和我的父辈》。
出生於1973年的小說家梁鴻,將此種追求具體在一件白襯衣頭上。她難以想象他們在農村生活的母親,為什麼會擁有一件永遠被清洗得乾乾淨淨的白襯衣,這也許是生活中這種意境的堅守。我關注到梁鴻講訴的那個細節,是因為我的母親也有一件同樣的白襯衣。
每代人的母親不盡相同,母親在被時代負面影響的同時,也刻畫了小孩的目標追求與夢想。
《我和我的父辈》的前三個單元《乘风》與《诗》是深邃厚實的,後三個單元《鸭先知》與《少年行》則是輕鬆風趣的。
吳京編劇的影片《乘风》所刻畫的母親,相對而言離當下遠一點兒,但影片通過一連串細節的展現與刻畫,成功地把抗戰時期的父輩形像,推到了現實生活當中。
我出生於1970二十世紀,我的父輩所處的二十世紀被飢餓與貧困困擾著,但在那么窮困的二十世紀,自己當中的許多人,依然有著對生活的追求。
但這足夠多形像地勾勒出那一代父輩的集體形像——自己悲觀,擁有一種閃爍的理想主義,是最值得被承繼的一種思想。
徐崢編劇的《鸭先知》,講的是首支電視節目廣告片誕生的故事情節。他出演的母親能代表改革開放後那一代父輩的形像,疑惑、衝動、敏感、膽大,自己被心底的夢想激勵著,被活耀的時代鼓舞著。自己的知識分子形像裡,也藏有實幹家的百折不撓,便是即使自己在這個時代的敢想敢幹,才開闢了一個好時代,自己的故事情節,值得被更多地講訴。
我企圖從《我和我的父辈》當中三位母親的頭上找尋共通點,發現能找出很多,但又難以更具體地把那些共通點講訴出來。“中國式母親”的群像臉孔,有清晰的另一面,也有模糊不清的另一面。在漫長的時間段裡,自己遊走於家庭與社會、職責與使命之間,努力地去爭取成為一位好母親。
本站關於電影海報,預告,影評,新聞,評論的綜合性電影網站,我們提供最新最好的的電影以及在線影評,業務合作亦或意見建議請電郵我們。(Copyright © 2017 - 2022 KKTM)。聯絡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