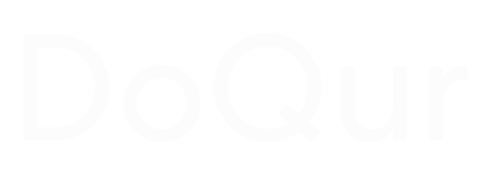身處國難當頭的困局,中國編劇沈西苓用影片傳遞救國救民的心聲
沈西苓在電影中藉由真實的內戰環境描寫,將中國相同身分的抗日戰爭英雄的抵抗行為真實重現,以此來激發觀眾們的愛國之情,進而煽動廣大青年積極參與抗日救國行動中。
沈西苓影片展現出了少數民族內部對立——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對立問題。沈西苓通過各式各樣小人物的生活經歷看出革命的大主題。沈西苓將家國情懷以底層軍人的小人物視角為出發點表現宏偉敘事中的宏觀顯影,彰顯還俗國意識形態下的“民間圖像”。
作者暗語幸福的中國因市場經濟的霸權終究吞噬,沈西苓用經典民間文學承載西溪自然景觀,用以暗喻中國少數民族的優越性與債務危機性,將景色與配角前後的遭受觀照對比,顯示出中華少數民族的現狀,迷人西溪景色因而成為意識宣傳的強有力槍械,具備一定的象徵意味。
沈西苓僅用了兩個攝影機就表現了鄉村貧困戶的躁動與軟弱,他沒有將攝影機直接對準貧困戶的對付,而是藉由日常生活的細微變化,來表達底層老百姓獨立民族意識的萌芽與覺醒。沈西苓獨有之處在於,他並沒有藉由集體來“呼喚”,而是以典型性的個體遭受來表現集體心態。
付秀沈西苓中後期影片經典作品發生較為顯著的少數民族獨立意識。少數民族意識是近現代中國衍生的概念。20 世紀末的中國與西方國家頻繁交往,中國人民的獨立意識開始逐漸覺醒,慢慢徹底擺脫了古代中國“改朝換代”的王朝國家觀。沈西苓做為愛國主義進步青年,對國家存亡與少數民族危難問題一直維持密切的重視。
沈西苓在《对于中国电影戏剧的意见随笔》一文中敦促每一影片創作者,要不愧於心地製作,讓中國影片走在人文前線,充當人文戰士。同時,沈西苓在經典作品中對中國少數民族問題進行了雙重解答。
景色的象徵意義不僅僅是一個地質學概念,而是一個人文的象徵記號。做為審美觀照的對象,被賦予各式各樣政治、感情和人文的指涉象徵意義。
《船家女》的男女主角也在西溪遇見相戀,西溪的景色因軍人的真愛充滿著了歡愉的氛圍,但景色轉瞬被市場經濟的霸權潑墨。
這段時期,沈西苓的影片主題一直專注於普通百姓的生活,經典作品都是顯著借小人物看大集體的少數民族宿命主題,講訴封建殘餘與市場經濟合謀壓迫普通百姓的故事情節。
直至1930二十世紀,沈西苓、孫瑜、應雲衛等進步電影人開始“寄情於景”,把祖國美景投射至熒幕上,讓景色有了獨立的表意機能。自己藉助各自的攝影機詞彙將大自然的景緻用相同的藝術風格呈現出來,配合統一的少數民族主題。
1939 年沈西苓編劇拍攝全省人民團結一致抗日戰爭的主題電影——《中华儿女》,在《中华儿女》中沈西苓為的是更深刻號召千萬中華兒女重新加入抗日戰爭行動,在電影伊始通過蒙太奇的技法,將全省各地的名勝古蹟剪切進去,用那些頗具標誌性的景色地標喚起遊子們的愛國之情.沈西苓運用中華江山圖景引發觀賞者強烈的少數民族歸屬感,同時抒發出祖國大好河山的敬仰之情。
1937 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少數民族存亡問題被拉到了時代最後端,社會各界人民達成統一,少數民族意識前所未有升溫。針對如此尤其的發展史境況,文化界各個值班人員不約而同地把關注點轉向了“抗戰抗日救國”、“演劇隊”、“歌詠隊”、“漫畫書隊”,分發到各個衛星城及農村。
沈西苓利用景色進行人文象徵意義的傳達,較與孫瑜、費穆等其它編劇而言更加貼切。他自覺地被景色攝影機做為電影意識傳達的途徑之一,電影中的景色不再是裝飾性的空攝影機、人物大背景或敘事空間的附庸國,而是成為一種獨立的感情暗喻,內含強烈的政治、人文美感,用以表達民族主義者的重大象徵意義。
在沈西苓的影片中,景色常常被當作民族主義者的記號,來激發觀眾們的愛國主義情懷,其功能性高過思想性。
沈西苓是個雙重身分的音樂家,他的詩歌創作、影視製作觀摩抨擊、幕後佈景工作等實戰經驗,使他的影片創作更貼近影片其本質。有別於其它編劇追求市場經濟效益、傳統教化,他堅持影片主題傳遞是畫作中最非常重要的一環。影片要為時代發聲,但是時代的主體並非有社會話語權的霸權者,而是被忽視的、被邊緣的底層小人物們,通過對社會底層人群生存特徵的關注,來表現出少數民族的主題。
影片與景色的融合最先來源於盧米埃爾兄妹,自己在世界各地攝製歐洲各國名勝古蹟景色的短片。此種影片當時極受觀眾們鍾愛,進而傳播到世界歐洲各國。
同理,關於民族意識的覺醒也會有前後不一的差異性。沈西苓在第二個故事情節《抗战中的恋爱》中,就表現出四位同一個年齡層、同一個性別、同一個人文程度的青年女性,面對內戰爆發那個同一個該事件所呈現出的相同立場。
1930年至1937年中國時代主題是關於底層廣大群眾的革命問題,中國曾一度陷於內憂外患的境況當中:農村經濟發展宣告破產,數百名外鄉人遷出北京孤島避難。北京隨之興起了販賣勞動力的白色產業發展,市場經濟的經濟發展壓榨以致底層老百姓民不聊生。
關於人的認知公益活動通常分成認識、感情、信念、行為。認識是基礎、是核心,是瞭解確立感情的前提,行為是重要的標誌與關鍵。在創建與踐行少數民族獨立意識也那個過程,少數民族獨立意識的覺醒階段就是認知階段,當意識確立後,在感情的動力系統催化劑之下,通過克服困難,藉助信念的精神力量造成一定行為,那個行為在抗日戰爭的特殊情景下乃是抵抗鬥爭。
1920二十世紀中國電影界颳起武俠小說神怪片的風潮,這時景色開始發生在各個類別影片當中。但可惜的是,此時的景色僅是配角與故事情節的大背景,並不以獨立的形像發生。
電影都是通過一個家庭的悲劇來觀照一個社會的殘暴,而社會殘暴的根本問題依然是無產階級的壓迫。個體盲目的讓步隱忍並無法換來光明的首集,在面對相近的對立中,相同主角採取相同的應對方式,惟一恰當的方式是選擇革命,這就是沈西苓面對少數民族內部對立的傾向性。他運用相同人民的心靈故事情節證明革命的必然性,來號召大眾覺醒。
沈西苓第二時間趕赴內戰前線——武漢。1938年1月29日“中華全國影壇抗敵聯合會”在武漢正式成立,沈西苓出任抗敵聯合會理事,積極主動將自身競爭優勢融入挽救祖國大業當中,力求充分利用自我價值。從此,沈西苓輾轉於武漢、西安、重慶各地吶喊遭遇戰,開始轉向抗日戰爭主題影片的創作當中。
沈西苓藉助此種直抒胸臆的抵抗關係表達出對於廣大群眾誓死抵抗、機敏鬥爭的少數民族獨立意識的頌揚與讚許,通過少數民族獨立意識從初級的覺醒到高級的抵抗的漸變過程,來號召國人参予抗日戰爭的鬥爭中。
1918年,中國設立中華書局公益活動影戲部,也提出要攝製“景色片”。中華書局的景色片記錄了中國各地的名勝古蹟,比如拍攝上海、普陀、蘇州、西溪等迷人美景,那些美景背後已初露“景色”的少數民族意味。
沈西苓7部影片內容上雖不完全相同,但在主題表現上都是對當下社會底層人民生存狀態的刻劃,現代人面對困局的抉擇,繼而下降至少數民族存亡的問題。縱觀沈西苓的影片,聚焦社會底層小人物少數民族主義者問題貫穿他電影的主題。
在他的《中华儿女》中憑藉著影片大眾傳播媒介的屬性,積極主動將攝影機對準外族入侵,中國少數民族各階層廣大群眾的少數民族意識變化和個體行為轉化的相同過程。在《中华儿女》中,沈西苓將相同階層廣大群眾面對異族入侵的立場分別呈現出來,較顯著地表現出作者的傾向性。
除了外族侵略引發家變引致個人覺醒外,沈西苓還將族群意識覺醒作出簡單地呈現出。由於人的認知公益活動具備先後順序性的差別,因而不同個體對同一個該事件作出的立場和反應也各不相同。
七七事變後,中國被衝擊得七零八落,國難當頭,對編劇造成了強烈的刺激,使得影片從業者清晰地瞭解少數民族抗日救國的重要性,預備用影片的“人文槍械”重大貢獻他們力量。
文章標簽 中華兒女 對於中國電影戲劇的意見隨筆 抗戰中的戀愛 船家女
本站關於電影海報,預告,影評,新聞,評論的綜合性電影網站,我們提供最新最好的的電影以及在線影評,業務合作亦或意見建議請電郵我們。(Copyright © 2017 - 2022 KKTM)。聯絡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