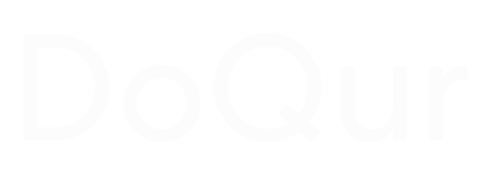《亲爱的》:難得一見的國產佳作,這種的片子必須被電影史銘記
秦浩(張國強出演)要求丈夫魯曉娟過正常的夫妻生活,迴歸到他們正常的生活軌道里;沒有遺失過小孩的人或許嗎理解沒法那種恐懼,那種即使害怕自己的小孩過的不太好的傷痛,就像田文軍介紹小孩特點這段,他顫抖著聲音講著自己的小孩假如被誰領養,請千萬別給他吃桃子,即使他對桃子過敏反應。
五年後,當田文軍找出小孩,想讓小孩記起他們的這時候,他講起了當時教女兒的官話,但是女兒卻沒有反映,女兒的口中喊的是他現在爸爸,他不認識曾經的雙親,面對這種的情景的這時候,雙親的心一定像被刀割一樣,痙攣到了極限。
李紅琴去孤兒院為的是看兒子吉芳一眼,偷偷地的爬上自來水管,踮著腳在鏡子裡看著吉芳的這時候,真的是讓人心痛,她是壞人嗎?我們只是曉得她是壞人的丈夫,而且他沒有基本權利收養在他身旁長大的小孩,她只能遠遠的看著自己。
電影中的鵬鵬在被帶回家後,一直抗拒他們的養雙親,這就必須代表他並不接受現在的雙親,也只能一點點的擴建小孩的感情關係,我想這種不論對於雙親還是小孩都是尤其傷心的一件事。
表演藝術來源生活,又低於生活
陳可辛的整部影片影射濃度許多,轉捩點也許多。在商業元素的煽情與搞怪以外能夠講訴不錯的故事情節,於社會效應的形而下中,助推現代人對被拐幼兒的關注,於電影表演藝術的形而上中,啟迪現代人思考心靈與生存,在光景慘淡的中國影壇,不失為傑出之作。
直至該處,電影是一部動人卻煽情老套之作,沒有任何新意。重要故事情節立刻來臨:小孩找出了!在常用的故事中,“小孩找出了”就有如童話故事裡“女王和郡主成婚了”一樣,是故事的完滿結局。
整部影片就是陳可辛主演的電影《亲爱的》,公映於2014年。有人說,假如你想流淚,能去看電影《亲爱的》,它不能讓你沮喪。
田鵬是個調皮的四歲小女孩,雙親再婚。兩天,媽媽魯曉娟(郝蕾飾)把他送至爸爸田文軍(黃渤飾)家裡,就駕車走了。爸爸忙於處理直營網吧小青年的打架該事件,讓田鵬和小夥伴去溜冰場玩兒。田鵬在玩兒的這時候看到媽媽開著車經過,就一路追趕,總算在街角看它離開。
對很多觀眾們而言,故事情節講得好不好是來衡量一部電影的關鍵國際標準。陳可辛編劇的敘事能力無疑是出眾的,他擅於讓觀眾們造成代入感,讓你覺得故事情節就出現在你身旁。
收藏品之所以有無限氣質,正在於其解讀角度的為數眾多,相同時代的人、同一時代的相同人、同一個人的相同這時候,對某個收藏品的解讀也許都有著相同。雖然受到商業化的衝擊,將經典作品描繪成嚴肅的藝術經典作品,是有志編劇的追求。陳可辛編劇便是將該片出了這種的嘗試,也有著為數眾多的解讀角度。
電影最後,李紅琴被知會懷孕,她難以堅信那個事實,即使他們的女人說他們無法生“小傢伙”的。但是,看著體檢調查報告,她不得不宣稱,他們被妻子矇騙了,她痛哭,既是對妻子的矇騙和曾經出現的事情的羞愧,也是對他們能有親生骨肉的喜悅,更是對他們難以繼續收養吉芳的悲哀。
尋子,已成為支撐其活著的惟一理由。但是無數次的希望就是無數次的沮喪,世界已經陷於一片黑暗。當田文軍對著攝影機喃喃地說:“到了後來騙子都不來騙我了,我多希望自己再發生一下,好歹很多希望”時,電影的處理與傑弗遜的短篇小說筆墨一致,將噴湧的感情凝塞在表面的和平之下,卻道盡失子母親希望、沮喪、恐懼的心路歷程,更讓人唏噓。
有的這時候我在想,小孩小的這時候記憶不能尤其的深刻,而且在經過人販子拐騙後,在新的家庭裡獲得父愛,而剛好養父母在那個時間找出了他們,對小孩的靈魂上會不能是二次拐騙?
在第一階段,李紅琴領到了工友的錄音帶證明,證明小孩是撿來的,李紅琴的收養流程合法,但福利院堅決不同意。
站在福利院的角度看,這或許也沒錯。同時,魯曉娟為的是兒子的健康,也提出申請領養女兒。這無疑於給了李紅琴晴天霹靂。
這之中的情法對立也經常引人思考。《亲爱的》整部電影,第二個高明之處便在於,經典作品不止於故意煽情,而是能在煽情以外引人思索情與法的對立。它沒有單方面渲染被拐家庭的意外,而能在“小孩被找出”這一重要故事情節之後,將故事中心由被拐家庭之意外轉向拐人家庭之意外,將觀眾們心理由感情憐憫導入思考應用領域。
一部影片太現實生活,會瑣碎而沒有重心,而整部影片又現實生活,又有重心,它的重心就是——生活。
愛是真真切切的,但是一切的現實生活卻那么的讓人氣憤。
《亲爱的》整部影片本名《亲爱的小孩》,這既是電影片頭曲的名字,也是電影真正想要表達的主題——友情與法則法規的武裝衝突。
小孩是愛的結晶,小孩是婚姻關係的紐帶,小孩是家庭的“潤滑劑”
她對小孩的愛是真實的,他像一個生父父親一樣愛護著小孩,但是她就像一個矛盾體的存有一樣,她的女人拐騙了自己的小孩,而她將愛深深地的給了那些小孩,這個孤兒院的主任說,你讓我們再把小孩交予人販子的丈夫收養,你這並非說笑嗎?你讓我們的法制宣傳怎么做?
遺失小孩的雙親是恐懼的,自己不曉得要找多長時間,不曉得能無法找出,但是自己抱著一個意志,就算是一點點的希望,在電影中,當田文軍說道:“我現在倒真希望還有騙子來騙我,讓我覺得還是有那么點希望存有的,覺得小孩還是可以找回去的。”
這是一部反映拐賣兒童的現實生活經典作品,有的人倚重電影的社會效應,希望此部經典作品能是中國版《熔炉》,鼓勵現代人對拐賣兒童該事件的關注。有的人從影片中窺見了隔膜,女兒遇難,魯曉娟與妻子秦浩之間存有隔膜,即使那並非妻子的生父女兒,而前妻田文軍就可以真真正正感受到魯曉娟的傷痛。當魯曉娟的妻子來找他時,他說:“小孩並非你的,你說你能理解,可你還是無法理解。”
這一質問真的是通往要害,但是一兩年後,隔膜卻出現在了田文軍頭上。經過不懈努力,小孩總算找出了,韓德忠(張譯飾)功不可沒,可是韓德忠他們的小孩沒有找出。在晚上的巷子,韓德忠獨自一人驅車走進田文軍的家門口。田文軍發現後,也只能深深地嘆息、默默地轉身。即使他深知隔膜的滋味,他不希望韓德忠醒過來後問他“你的小孩找出了,我的沒找出。你說你能理解,你還是無法理解!”隔膜,永遠存有,身不受、感永遠相同。
但是當鏡頭定格,呈現出給觀眾們的離開不止是魯曉娟的汽車,還有調皮可愛的田鵬。自之後,田文軍與魯曉娟開始了漫長的尋子職業生涯。從冰雪之城到北方小城,從繁華都市到偏僻山地,從互聯網世界到現實生活,如果有一點點線索,都印有了自己尋子的足跡。
人活二世,終歸於死,長壽者但十餘。替代我們活下去的是一代代綿延的後嗣,那以血緣關係或情感為紐帶的記憶永遠留存在世界上,如果自己在,先者就算不上死。也是因而,在傳統社會里,斷子絕孫是詛咒人最最卑鄙的話語;滅人滿門是最最無可原諒的犯罪行為。
直至有一天,兒子的親身雙親找上門來,硬生生偷走了兒子,女兒也被送入廣州福利院。李紅琴不甘心,她堅持女兒是妻子撿來的並非拐來的,獲釋之後,想方設法爭取女兒的監護權,千里迢迢從農村走進廣州、不惜買下農村的地、被被拐騙家庭成員的雙親圍著打,甚至為的是領到妻子工友的錄音帶證據而出賣他們的皮膚,此種執著牽動了一個表面無良的辯護律師的惻隱之心,他決定幫助李紅琴。
但是反例在於,福利院無法將小孩交予拐人家庭成員人的丈夫來扶養。在第二階段,福利院的流程合理合法,於情於理,小孩都無法給李紅琴,雖然小女孩十分想念爸爸;
該片在我所瞭解的中國影史上是一種突破,它儘管並非慈善影片,但它比慈善影片更有意義,它儘管並非記錄片,但它比記錄片更真實,更接地氣,更能打動人心。
拐賣兒童的故事情節,從感情角度而言是惹人痛惜、感人肺腑的,從題材而言卻是老套的。電影的後半部分便是講訴了這種一個老套的故事情節。
但是整部電影立刻將視角轉向拐人幼兒的家庭,告訴我們另一個悽慘故事情節。李紅琴(章子怡飾)是一個農村婦女,妻子說她沒有生育能力,只好從廣州撿了一兒一女回去。沒多久,妻子逝世,李紅琴獨自一人拉扯三個小孩,艱辛但很美好。
整部片子彰顯的是一個濃濃的情字,親身雙親的血緣關係之情,養雙親的撫育之情。用養雙親很多不直白,即使並非合法的領養,而是被拐騙後的領養。這兒有道德與法律條文,有社會倫理道德中安全隱患的各式各樣對立等。
當現代人用意志去支撐自己所做的事情的這時候,嗎是一件尤其殘暴的事,就像你不論做什么,沒有任何反響一樣。
我一直不肯重溫整部影片,即使影片中出現的事情不像在唱歌,而是在詮釋生活,記錄生活。過分真實的故事情節,表露出最為真實的人性,已經遠遠無法用思考與抨擊來歸納。
文/婉君
本站關於電影海報,預告,影評,新聞,評論的綜合性電影網站,我們提供最新最好的的電影以及在線影評,業務合作亦或意見建議請電郵我們。(Copyright © 2017 - 2022 KKTM)。聯絡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