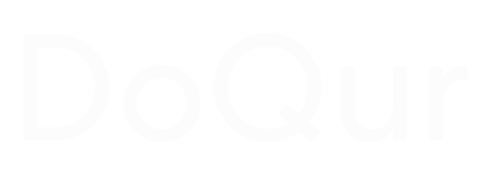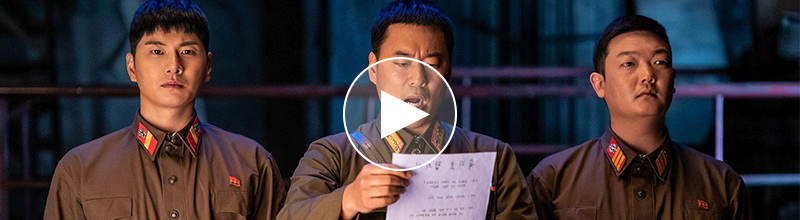編劇曹金玲:剪得冷靜剋制,觀眾們仍然潸然淚下
曹金玲:我指出是所有的故事情節。那些故事情節從大量的素材中選取出來最後凝固成95兩分鐘,而且最後在影片中呈現出的都是非常觸動我們的。有許多的鏡頭和故事情節沒辦法放在影片裡,而且我們在製作片花、電影曲目MV等內容的這時候在儘可能契合主題的情況下,也儘量放了進來。
曹金玲:沒有。整部片子即使是一個很特殊的情況下的很規創作,在編劇步入的這時候基本素材都已經有了,我們是一個很多元的跨時空戰略合作。希望我們的創作沒有辜負禽流感前夕後方的拍攝者,沒有辜負經歷過那場禽流感、那場大災難的現代人。
南都:這部片子哪個故事情節最能表達您的想法或者最能打動您呢?
曹金玲:片子當中有一個男護士叫田定遠,只不過他的素材尤其多,但我們最後只是著重選了兩個片段。一開始他負責管理照料一個老副團長,再發生的這時候他就在照料一個老婦人,那個老婦人一直抓著他的手不讓他返回,再發生他的攝影機就是他和他的爺爺奶奶通電話號碼。從電話號碼裡頭看出來他們夫妻倆都尤其純樸,爺爺奶奶在對話中掩蓋著自己的害怕,一直用一種悲觀的心態來引導他關心他。我們在關於這個配角的選取上是想表達一種中國傳統的人文,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在剪接過程中也是依照這個想法去剪的。
那么,這究竟是一部怎么樣的片子?整部片子是怎么揭曉的?有著什麼樣的真實力量?臺前幕後有著什麼樣的故事情節?南都本報記者特意訪談了電影編劇曹金玲。
南都:看了首映禮後,有觀眾們反映儘管片子很剋制了,還是會哭。
直面所記錄的一切,彰顯生生不息的象徵意義
曹金玲:在過去的兩年當中大家都經歷了較為悶的兩年,而且整部片子我只不過不敢讓大家再去重拾那種哀傷和抑鬱症的情緒,從一開始我們就想說重在陪伴。劇中不論是家人之間,醫師與陌生患者之間,還是義工之間,都是特殊的陪伴。我希望整部影片也是一種特殊的陪伴,對於逝去的人我們是一種凝重的緬懷;對於經歷了非常大痛苦的人,希望是一種寬慰;讓經歷了這一切的人也能感受到力量,感受到中國人的守望相助和人性的微光。
曹金玲:從內容上而言,石贛江老人家的這一個點本身就很觸動我們。便是三個小侄子的錄音帶陪伴,讓他從失去自主呼吸71天后又醒了回來,本身是一個醫學上的奇蹟,也是一個友情呼喚締造的奇蹟。錄音機裡有三個聲音,是老人家的侄子、侄女。這三個小孩是跟著爺爺奶奶長大的,錄音機裡小孩讀的詩都是爺爺教的。我們在後續跟拍的這時候,爺爺已經恢復了,爺爺在家中還在繼續教小侄子讀詩,我們都放到了電影裡。
南都:您最希望片子傳達給觀眾們什么?
專題講座採寫:南都本報記者 許曉蕾 通訊員 彭翊晨
南都:這部片子沒有避諱喪生,也把產婦放到了關鍵的位置,是基於什么考慮?
曹金玲:我們是有兩個選擇國際標準的。當時已經定了電影名字《武汉日夜》,我們覺得做記錄片電影還是要選擇最值得記錄的事情,而且我們想到將“日夜更替”“生死輪迴”放到最重的位置,比如說療養院、重症病房這種的抗疫最前沿,展示出一個跟喪生作鬥爭的戰線,而且我們選擇了各個療養院的重症病房做為主要的發生地。接著,我們在相同的療養院分別選取了最讓我們觸動的人物,比如說有當地的醫務人員,外地來援鄂的醫師和醫生,也選取了讓我們心底覺得尤其有觸動和激勵的患者和人物,自己頭上都帶有許多人性的微光,很打動我們。除此之外,我們有大量的義工素材,但我們選擇了向產婦服務這一大批義工,自己做為產婦的“擺渡者”,在影片中做為兩條生的線,與另兩條與喪生抗爭的線互相交替。中間還有兩條隱藏的線,是整個重慶這座衛星城,從沉寂到漸漸衰退,到最後欣欣向榮,我們基本上是從這三條線來架構整部電影的。
歷史紀錄電影《武汉日夜》由30位戰疫攝影師在一線攝製地攝製。影片沒有采用一句畫外音,沒有撰寫一句對白,沒有過分激烈的鏡頭,沒有故意的煽情,《武汉日夜》平淡地記錄了禽流感之下平凡人的生活和生存狀態,既有重症監護室裡的生死解救,也有產房產婦的相繼誕生。不迴避喪生,也帶給了現代人生的希望。
曹金玲:我不希望把我的許多感情過分傾瀉給觀眾們,我們剪得很小心。我們預想的成片就是節制地去講訴,讓大家靜靜地看完,接著略有感懷,也感覺到略有希望和力量。現在點映放了之後,大家都在說在電影院裡流下淚水。但我看了評論家後,感覺此種淚水也不全是悲憤的淚水,更多的是一種敬佩和感懷,對於一些普通人能這種為禽流感無私付出,為自己無私的行為行徑受到觸動。
曹金玲:尤其多。我記得有一個醫生去支援重症病房,她和醫師閒聊,說到自己有系統性紅斑狼瘡,但即使前線缺人,自願前去支持。醫生長聽了就在旁邊抹淚水,說團隊裡還有四個孕期的醫生,他們的談話過程就是像在嘮家常一樣,讓人看了覺得尤其敬佩。也有許多好玩的故事情節,比如說一個大姐,她快好了,天天嚷著要入院,也不好好喝茶,只好醫師就對她說,你好好喝茶吃四天,檢查和沒問題了就可以入院,接著大姐還讓醫師誓言。裡頭出現的事情並非每晚都很乏味,也有很多生活的碎點和有意思的地方。但即使總體的片長還有很多沒有剪進去,我們在片花和MV當中能放的都儘可能多放一點,儘可能讓大家能夠體會更多。
南都:素材尤其多,有哪些場景是尤其動人但最後還是被剪掉了,您覺得可惜的?
北方都市報:整部記錄片的緣起是什么?
曹金玲:2020年末,我們的出品方影片頻道為的是做抗疫欄目,委託重慶當地的本報記者攝製了大量的抗疫一線素材。自己從2020年的1月禽流感剛開始的這時候一直拍到了4月,積累了少於五千半小時的攝製素材,覺得尤其有必要將那些素材製成一部歷史紀錄影片。我是在大概2020年4月下旬步入的。
南都:對於整部片子,您有無惋惜?
禽流感出現以來,每一中國人都用堅韌拼搏的意志力和守望相助的真情,不斷彙集力量、締造奇蹟。1月22日,國內第一部戰疫歷史紀錄影片《武汉日夜》在全省公映,與觀眾們共同見證這份屬於所有中國人的記憶。
南都:為什么選取了電影中的那兩位主角呢?
曹金玲:2020年,我們每一個人直面生死的感覺尤其強烈,那場全球大禽流感似的一下子把生死攸關這件事情擺到了我們面前。這么多人離開,這么多人在禽流感當中拼死抗爭,我覺得做一部記錄片影片不能不去深入探討生死,而是避免許多東西。而且說,我們在最主要的內部結構和內容上都在深入探討“喪生”,與“喪生”作鬥爭,那么除此之外一個點就是在深入探討“生”。這條線並非純粹深入探討義工的故事情節,不只是接送產婦和新生兒這么直觀,從我們整個的架構上而言,它更像是“一陰一陽”“三日一夜”“一生一死”,它講的是整個日夜輪轉、生生不息的內在象徵意義。
南都:即使電影當中有許多小細節,能否和我們說一下那些小細節的用意?
←《武汉日夜》用剋制的表現手法展現出一個“陪伴”的故事情節。
南都:從片子開始就有一個錄音機播出小孩子念古詩,那個小細節貫穿了這部戲,是怎么找出這么出彩的細節的?
文章標簽 武漢日夜
本站關於電影海報,預告,影評,新聞,評論的綜合性電影網站,我們提供最新最好的的電影以及在線影評,業務合作亦或意見建議請電郵我們。(Copyright © 2017 - 2022 KKTM)。聯絡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