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雀雀專欄】2019 年臺灣影片的《上半場》
拍電影像是生孩子,孩子生出來的那一刻,就開始是個獨立的個體,有自己的命。而在 2019 下半年,《下半場》太適合作爲臺灣電影 2019 年下半場的新生代言電影。
臺灣電影今年上半年超冷清,在票房上至今「零破億」。十年來,繼 2017 年之後,賀歲檔期必有破億國片的紀錄又被打破一次、落空了一次。《下半場》會否像 2017 年的《紅衣小女孩2》一樣、成爲年度首部破億票房臺片?答案尚且不得而知(兩片都是在暑假的八月底檔期上映),但《下半場》體質強健,與今年上半年水準參差的商業類型國片確實不同,值得臺灣觀衆再給國片一次進電影院捧場看戲的機會。
猶記得《下半場》導演張榮吉的長片處女作《逆光飛翔》裏的主人翁黃裕翔,他是個眼睛看不見的孩子。知悉了有些看不見之人能感受到「光影」,導演遂把《逆光飛翔》拍成爲一部充滿光影語言的故事。而《下半場》的主人翁姜秀宇是個需要戴助聽器的籃球男孩,阿吉導演也就理所當然地把《下半場》拍成一部充滿聲音語言的電影了。
【用聲音語彙豐富敘事的情感醞釀】
一般電影常以對白作爲敘事主線,但《下半場》的聲音敘事語彙是超越對白語言的。第一場籃球比賽,是姜秀宇(範少勳飾)和姜桐豪(朱軒洋飾)兩兄弟靠打街頭鬥牛賺錢的戲。哥哥的助聽器一度被撞飛,觀衆隨即感受到耳鳴與在真空中聲悶慢透之感,導演沒弄痛觀衆的耳朵,但是可以清楚感受到哥哥姜秀宇聽不太到而有點發慌了的那種程度。
回家後,弟弟手錶鬧鈴響了,提醒哥哥「助聽器該充電了」。弟弟的手錶鬧鈴在全片中一共嗶響過三次。第二次是在兄弟離家出走的晚上,他們沒地方充電,弟弟於是開始顯得有點懊悔,是他和叔叔起了衝突,哥哥纔跟他一起離開寄住的叔叔家的。第三次是在兄弟分開了好一陣子以後。爸爸因工受傷住院,哥哥找弟弟一起去醫院,但弟弟堅持留在球場上比賽,賽後趕到醫院被哥哥揍,哥哥打完轉身離開,在那個時候,弟弟的手錶鬧鈴響了,在空蕩的樓梯間裏,那嗶嗶鈴聲顯得那麼孤單而充滿想念。與此同時,被留在原地的弟弟哭了,最終他還是沒能提醒哥哥充電。他回到菁英球隊繼續練球,因受傷被教練臭罵,他無奈地問同樣也受傷的學長:「我只想要把球打好而已,真的那麼難嗎?」
姜秀宇在學校時,有場愛情正在萌芽。那女孩子講話的聲音特別輕柔,最充滿感情的時候都是用氣音小小地說,在幾乎要聽不見的音感中反而彰顯了悸動氛圍。不論是跟着一起罵「臭弟弟」抑或是在冠軍賽的人聲鼎沸中對姜秀宇用口語輕柔地說「加油」。反正姜秀宇很大的機率是聽不見的,聲音的傳遞不切實際,表情和心意反而最真。
但既然是運動電影,當然少不了「大聲話蝦」。初次上場打 HBL ,姜秀宇一開始還不知道很久沒見的爸爸來看他比賽。他上半場打得很爛,直到聽到父親大聲加油的聲音傳過來的那個當下,被親情隊友情和愛情滿滿包圍的姜秀宇纔在下半場開始贏球。後來光誠打進決賽,教練陳書文(段鈞豪飾)上臺精神喊話,全校忍不住一起哭着齊喊「光誠,加油」,話蝦之真切,甚至比冠軍賽場上的衆聲震耳欲聾還要感人。大聲小聲落玉盤。《下半場》每個從無聲到有聲的時刻,都是一次電影聲音的魔法展現,歷史上從無聲電影變成有聲電影,爲的不也就是這一份激動人心。
【快慢影像抓得住觀衆的高標運動電影】
早在《逆光飛翔》中練過影像敘事的張榮吉,一度在《共犯》的類型裏更進一步嘗試將電影畫面風格化的可能。
這一次在《下半場》,阿吉導演所面對到的是更硬核的動態影像敘事技術考驗。而他其實早已與楊力州導演一起拍過實戰比賽的足球紀錄片電影《奇蹟的夏天》。運動電影的影像會被放大檢視,演員球員的動作表情有沒有做到對?教練交代的戰術有沒有被具體實踐?大型運動盛事的熱鬧場面特效是否禁得起細看?乃至於攝影剪輯的節奏是否有踩到觀衆的感官痛點?在《下半場》的劇尾冠軍賽那短短的 25 分鐘裏面,張榮吉導演神奇地讓主人翁們帥氣地都做到了。達標之餘,還不忘做了背景快動作對照角色慢動作、聚焦其情緒展現的融合同框畫面,讓衆人皆醒而兄弟與觀衆獨醉。
這份渲染並非其來無自。這對兄弟,是在很清楚的畫面語言之中,逐漸長大成爲想要變成的自己。每一回當光誠籃球隊一羣人在訓練、受罰,或者是歡樂笑鬧之際,對照剪輯進電影裏的,是弟弟姜桐豪在育英僅一或兩個人沉默地練球或受罰的畫面。在育英,學長是一個個高高在上的存在,小高一的弟弟要幫忙撿球、收拾休息室;在光誠,學長是一隻狗,哥哥是負責溜狗撿大便的小高一。
但哥哥也因此溜出了一段戀曲。那個女孩是游泳隊的,就像是《藍色大門》的張士豪。晚上裏男孩與女孩的幾次泳池見面,複製了《藍色大門》的青春曖昧詩與溼;另一方面《下半場》卻也用了弟弟在片頭鬥牛賽的一幕回頭慢動作畫面,交代了哥哥視角與心中那份不言自證的友愛與嚮往。不論《下半場》這樣拍有無自覺,都可算是師承自易智言師傅的陳大璞導演的精采復刻。
【當哥哥拿掉了助聽器】
對於聽得見聽不見,哥哥的教練另有一番見解。在練習和比賽的碰撞之中,姜秀宇的助聽器總是會掉。後來,教練問他,要不要試着不要依賴助聽器?這對姜秀宇而言是種拔除掉安全感的赤裸上場。光誠是一支沒有資源、沒有明年,即將解散的籃球隊。教練總在提醒他們「沒有退路,以後只會越來越艱困」,又愛問他們爲什麼要留在球隊?孩子們愛打球的原因有很多種,不論如何,可以確定的是,光誠的這羣孩子沒資源、沒退路,但還是留下來打球。
看《下半場》時,我想起了臺灣電影。每個臺灣導演都只是想要把電影拍好而已,真的那麼難嗎?這兩年的臺灣拍片環境越艱困是大家心照不宣的認知,但還是有人留下來,還願意拼到下半場。在下半場,拼冠軍賽的姜秀宇不一定會戴上他的助聽器。我不能說助聽器就是臺灣電影輔導金。沒有助聽器當然會慌,但在球場上,資源捉襟見肘的姜秀宇,是真的很想贏過待在豪華球隊裏的姜桐豪。拿掉助聽器是種面對自身現實條件的誠實,更可能是一份壯士斷腕,反正那隻聽不見的青蛙也是因此才跑得那麼遠的。
《下半場》裏所講的光誠中學困境,就像是當下臺灣電影的處境。電影是個平臺,像光誠教練站上臺去、所說出的這羣年輕人的心聲:「我們是一支即將解散的球隊,曾經有人不看好我們,甚至要我們放棄,但是有一羣人並沒有放棄」,《下半場》裏面的每個年輕人也都如教練所言:「他們每天要在球場上流下多少的汗水,忍受多少的疼痛,甚至還有挫折和否定,但是我發現他們一天一天比昨天更強。」是啊,如果他們都還沒有放棄,你們怎麼可以先放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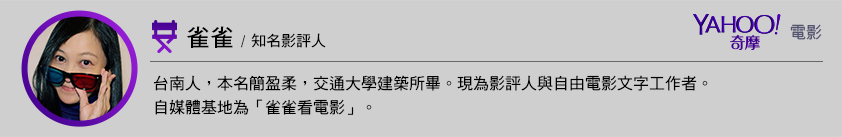

本站關於電影海報,預告,影評,新聞,評論的綜合性電影網站,我們提供最新最好的的電影以及在線影評,業務合作亦或意見建議請電郵我們。(Copyright © 2017 - 2022 KKTM)。聯絡我們









